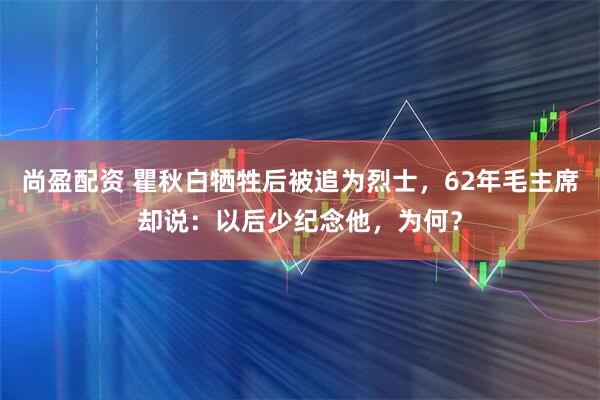
“1962年7月的一天,北京,毛主席放下手中文稿,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轻声说:‘以后少纪念秋白。’”话音不高尚盈配资,却立刻传遍中南海的长廊。许多人听到后皱眉:这是怎么回事?不是早在1945年就被追认为烈士吗?带着困惑,几双目光追随文件袋在案头慢慢合上。

把镜头往前推,瞿秋白189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,科举末期书香门第的最后一代。父亲好画,母亲好诗,家中常以“七步成联”逗孩子。幼年的他握着狼毫写大字,也随伯父刻印章,一派世家子气象。可惜辛亥革命后一切扶持骤停,父亲官途断绝,家境随之倾颓。1916年,母亲因贫病自尽,这道伤痕日后常在他文章里隐约浮现。
生活逼着他南北奔走。1917年,他来到北京,原想叩开北大,却因学费问题折返,最后进了俄文专修馆。也正是这一转弯,让他得以远赴莫斯科采访列宁。那一年,他才二十四岁,手里握着速记本,而对岸的红场正铺开崭新的政治实验。回国后,他把见闻写成《赤都心史》,国内知识界第一次通过汉字窥见十月革命的细节。宣传才华由此显山露水。
1923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,瞿秋白常与毛主席在广州、上海、武汉等地碰头。两人年岁相仿,一个北方湘音,一个吴侬软语,讨论起农村运动与文化启蒙时,常能通宵。“毛润之尚盈配资,我看农民起来是大势所趋。”——这是瞿秋白在广州黄昏里对毛主席说过的话,冯雪峰后来回忆,这话喊得中气十足。

大革命挫败后,潮水退去,各自站位不同。1928年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,妻子杨之华和女儿小独伊随行。那三年,是他生命里难得的宁静。郊外草地上,小独伊采来野花递给他:“爸爸,闻闻!”,他会弯腰把花别到女儿发梢。可宁静不等于脱离斗争,王明集团对他的排斥自1931年显现,他被边缘化的同时,也被贴上“富于感伤”的标签。
1934年秋,他奉命潜回江西苏区,担任临时政府教育人民委员。重返前线前,他意识到肺疾加剧,提出带妻女同行,却被拒。那一夜,他在上海霞飞路小公寓里抱着女儿,窗外车灯将父女身影拉得很长。朋友劝他暂避,他只淡淡一句:“工作召我,总要有人去。”

1935年2月,中央红军已踏上长征,他因病留在闽西。3月被国民党搜索队捕获尚盈配资,关进长汀监狱。敌人轮番审讯,软硬兼施。蒋介石放话:写一份自白书就放人。瞿秋白回答两个字:“不写。”为了表态,他反而提笔写下《多余的话》,剖析自我,也记录内心的动摇与苦闷。书稿送出监牢后,被国民党机关报偷偷删改发表,引来外界种种曲解——有人说是“忏悔书”,更有人借此给他扣上“叛徒”帽子。
6月18日清晨,刑场设在长汀西门外的松树林。由于肺病,他连站立都费劲,向刽子手提出两点:不下跪,不击头。于是,他盘腿坐在青草上,高唱国际歌,子弹瞬间洞穿胸膛,年仅三十六岁。那首《国际歌》的中文译本,正是他几年前完成的。

同年秋,正在途中的毛主席听闻噩耗,对冯雪峰说:“这下,你失一友,我亦失一友。”简单一句,足见情分。1945年,中共七大正式追认瞿秋白为革命烈士。新中国成立后,教育部将他的文章列入教材,上海、常州纷纷修馆立碑。直到1962年的那句话,让许多人难以理解。
要搞清缘由,先看当时的大气候。1962年初,三年经济困难刚过,全国上下需要振奋士气,强调顽强意志与乐观精神。瞿秋白的《多余的话》在情绪基调上并不明朗,“孤独”“怀疑”“自检”这些词不利于塑造那种昂扬氛围。相比之下,方志敏的《可爱的中国》充满对未来的必胜信心,更符合宣传口径。因此,毛主席提议“少纪念秋白,多宣传方志敏”,从策略层面看,并非否定瞿秋白的功绩,而是一种宣传侧重。

此外还有一个细节容易被忽略。1950年代末《多余的话》在港澳流传,一些反共刊物加了煽动性注释,再度把“瞿秋白=忏悔者”放大。对外斗争形势紧张,中央对意识形态渗透颇为警觉。为了避免敌对势力借瞿秋白的话做文章,减少公开纪念就成了务实做法。换句话说,“少纪念”不代表“降评价”,而是防止被对方当筹码。
作为读者,我认为毛主席的这句嘱咐更像临时策略而非终极定论。事实证明,进入改革开放后,《多余的话》重新整理出版,学界对瞿秋白的地位再无争议,党史研究也把他与陈独秀、李大钊并列为早期重要理论家。如今常州的瞿秋白纪念馆里,那把当年他坐在刑场上的竹椅依旧摆放。解说员说,椅子腿有被子弹剐出的缺口。我驻足良久,想到他唱出的那句“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”,依旧铿锵。
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翻涌的河,瞿秋白显得复杂而真诚。他宣讲马克思主义时锋芒毕露,写《多余的话》时又坦率呈现软弱。正是这种不加掩饰的人性,让他与后来被塑造成钢铁化的“硬汉”形象拉开距离。或许毛主席当年担忧的,正是这种“过于真实”在特定年代里的冲击力。

时间来到2024年,站在常州人民公园的一隅,老人们晨练间仍会提起秋白。“那位写文章厉害得很,枪口下都还背着普希金呢。”他们口中的敬意,经过岁月过滤,显得平和又笃定。英雄或许可以少宣传,但历史永远会记得。
联丰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